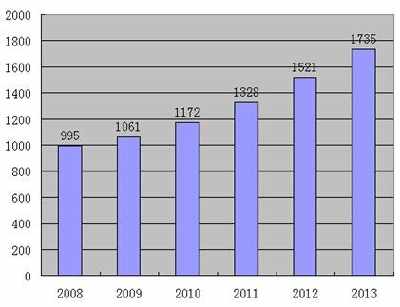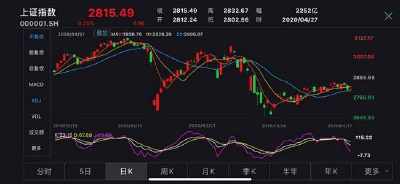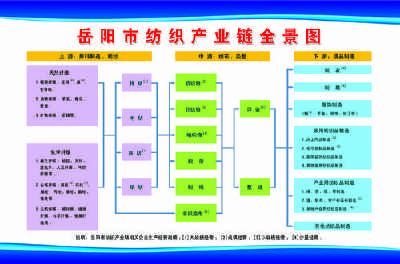早上,我听到远处杜鹃在唱歌。
布谷鸟怕人。它通常不进入居民区或飞往村庄。它的大部分电话来自远方。
布谷鸟的学名是布谷鸟。
杜鹃有很多种,有大杜鹃、四声杜鹃、八声杜鹃、中杜鹃、小杜鹃、鹰杜鹃。大杜鹃是两种杜鹃的一种。它的声音是单调的,即连续的布谷鸟、布谷鸟、布谷鸟、布谷鸟。从容不迫,从容不迫,听起来很温柔。只从语速上,听不出催人播谷的意思。
中国古诗中提到的杜鹃是四声杜鹃,也有子贵和杜宇的名字。因为杜鹃花的口膜上皮和舌的颜色是鲜红色的,它叫的时候,古人认为是哭血;血流到地上后,变成了红色的杜鹃花。所以布谷鸟这个词同时指的是两件事:一是布谷鸟,二是杜鹃花。
古代诗人经常把这两者一起背诵。南唐诗人程把两者的关系写得很清楚:“杜鹃花与飞鸟,何怨美?”它满嘴是血,滴进枝头和花朵里。李白的诗是:“蜀中曾闻秭归鸟,而宣城亦见杜鹃花。三月一呼、一回肠、一歇、三泉、三杠。“其中,子贵说的是杜鹃鸟。李白在宣城看到杜鹃花,自然联想到蜀中的紫桂鸟。这说明在李白的时代,花鸟可能同名。
然而,宋代杨万里并不认为杜鹃花是杜鹃鸟的血染的。他说:“你哭的时候为什么哭?准时偏向布谷鸟的声音。傅嘴里有多少血,我怕会让人哭出来。”带着露珠和红泪的杜鹃花是怎么产生的?只有当它开花时,它才与那里的杜鹃叫声相吻合。杜鹃嘴里能有多少血?杜鹃花的颜色恐怕是被无数泪水染过的。鉴湖女子秋瑾也写了一首两首诗:“杜鹃啼如血。应该是春天不能久留,晚上风冷。”在这首诗中,有一股冲击波。
杜鹃的另一个名字叫杜宇。这名字来自古代蜀国的一个传说。古蜀国开国国王名叫杜宇。他帮武王伐纣以后,称帝于蜀,叫望帝。他晚年时,蜀地发生了大洪水,其相鳖灵治水立下了大功。杜宇为表达对鳖灵的感谢之意,就将王位相让,自己化成了一只鸟。每到春天,就要不住啼鸣,呼唤人们“快快布谷”,蜀人听见了就说“这是我们望帝的魂啊”,于是呼鹃鸟为杜鹃,意思是杜宇变成的鹃。李商隐那句著名的诗“庄生晓梦迷蝴蝶,望帝春心托杜鹃”,说的就是这个典故。四声杜鹃的鸣声是“gū-gū-gū-gù”,这四个音节让古今中外的人附会出了许多不同的意思。
在说英语的人听来,它像是“one more bottle”(再来一瓶),或是“brain-fever”(脑子发热,或脑膜炎)。有的地方就直接把这种鸟叫“brain-fever bird”,这名字让人忍俊不禁。
在说汉语的人听来,它的叫声像是“不如归去”“光棍好苦”“快快播谷”“快快割谷”。这么一联想,四声杜鹃的鸣声里就被赋予了幽怨思归和催人播种的意思了。
有人说,客家人听这四字是“滑哥煲粥”。对这一说法,我也感到新鲜。为了求证,今天我专门请教了一位客家朋友,叫她用客家话发“滑哥煲粥”这四个字的音,我听了一下,感觉也确实接近四声杜鹃的叫声。这位朋友还进一步介绍说,客家人把鲶鱼叫“滑哥”,用鲶鱼去皮切片煲出的粥挺好喝的。这说明,“滑哥煲粥”是客家人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种饮食。怪不得客家人会听成这四个字呢。
客家人,是在秦代、西晋末年、唐朝末年和南宋末年,因战乱从河南和山西等中原地带移民到南方的汉人。客家话,是中国七大方言之一,一般认为,它和中古汉语之间的承袭关系较为明显。用客家话朗诵唐诗、宋词,韵律方面的吻合程度比用普通话读要高得多。客家人的话里,包含着唐宋时代黄河流域的汉人说话的遗风。从这点来说,四声杜鹃发出的“滑哥煲粥”四个音节,还颇有古韵呢。
但我问那位客家朋友,客家话“不如归去”四字的发音与“滑哥煲粥”是否相同,她说不同。客家话里没有“不如归去”这话,她也从没说过这四字;我硬让她读,她就读得有些犹豫、拗口。这也难怪,客家人南迁以后,客家方言已与闽、粤、赣等方言高度融合,中原地带的音韵很多已经遗落在秦汉唐宋的历史长河中了。“不如归去”,可能只是北方汉人听出的鸟声吧。
据说,说粤语的人听杜鹃的叫声像“家婆打我”。正好我这客家朋友还是广东人,我就请她用粤语说这四个字。她说了后用微信语音发给了我,我一听,还真是接近四声杜鹃发出的鸣声。
四声杜鹃的鸣叫实际上挺好听的,可能这叫声是乐音吧。英国博物学家吉尔伯特·怀特,在他的《塞耳彭自然史》中曾提到,他的邻居测试到布谷鸟的叫声有三种,一是D调,二是D大调,三是C调。
我不懂音乐,也没做过类似的测试,但我感觉,像杜鹃、画眉、翠鸟这类叫得好听的鸟,是能叫出和弦的。而麻雀、花喜鹊、灰喜鹊,则只能叫出噪音。
至于鸟的叫声到底是啥意思,恐怕只有人家鸟自己知道,我们人类听着像什么,不过是我们人类的穿凿附会。比如,今天早上,我听到滴滴水的叫声是:“就你能闹,你就这样,你这,算了吧。”它来来回回发出的就是这几个音节。但我知道,人家说的根本就不会是这意思。
人要是像孔子的女婿公冶长那样能听懂鸟语该多好。那样,人往树林里一站,就能知道鸟们在说什么了。现在,人们都是以人之心度鸟之腹,度不到正地方。
橡杜鹃这样的鸟们,很少窃窃私语,它们彼此说话的声音很大。在这一点上,麻雀更甚,好像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开讨论,找对象啦,生气斗嘴啦,或谁对谁有意见啦,全是大声说出来。
看起来,鸟们没有隐私,很少耍阴谋,做鸟从来是坦坦荡荡,清清白白。它们似乎也没有法律,所有的行为都被许可,所以做事就不用藏着掖着,不用耍心眼儿。比如一只小鸟刚捉了只虫子,大鸟看到了,就直接飞来抢去。抢去也就抢去了,没有鸟认为这有什么不对,也没有鸟出来伸张正义,打抱不平。哪怕一只鸟杀了好几只鸟,也没有别的鸟来惩处它。有时,做了坏事的鸟不光受不到惩处,还能得到好处,这样,做坏事甚至还会成为传统。
杜鹃其实就是一种祖祖辈辈爱做坏事的鸟。
杜鹃属于巢寄生鸟。有人统计,三分之一的杜鹃自己不养活孩子,都是把蛋下在画眉、知更鸟、苇莺等鸟的巢中,叫别人代养。她会趁着别的鸟外出时,赶紧跑到别人的窝里产下一枚蛋。杜鹃的蛋呢,又孵化得早,小杜鹃一出生,就先把别的蛋啄破,或把别的蛋、刚出生的小鸟推出鸟巢,自己独享养母的喂养。因为它不久个头就能长得很大,需要的食物相当于三四只其养母亲生的幼鸟进食的总量,所以它得保证养母除了自己之外不会再养别的孩子。而那可怜的养母呢,本来都身材瘦小,这时就只有拼了老命才能为这养子找够吃的。她受的这累全是为自己的智力付出的代价:刚开始自己窝里多了个不一样的蛋她也看不出来,后来看到自己养的孩子跟自己长得完全不像也不去想一下是咋回事,自己的孩子被养子谋杀而不自知,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把杀人犯养大了,自己还累得跟孙子似的。
有时感觉,鸟的世界,就像鸟的头脑一样简单。
鸟们要是见识过人的世界中事务的繁琐,该多么不解。它们肯定认为人是一种做事效率最为低下的生物。大部分的时间,人都用来攀爬,用来创业,用来挣钱,用来出名,用来诤讼。为什么不像它们一样饿了时候再去找顿吃的,吃完了就去晒太阳、乘凉、理理羽毛、聊聊鸟事?
鸟们不像人类,既要操心来处,又要忧虑去处,面对当下时,又要攻攻杀杀,争争夺夺,尔虞我诈,妒强欺弱,没有一刻的消停。鸟们比人类出现得早,它们在地球上的历史比人类都长。但没有鸟去关心历史,也没有鸟在意未来,从这点上来说,它们都是活在当下的动物,是最有佛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