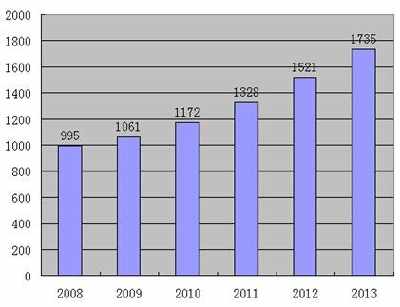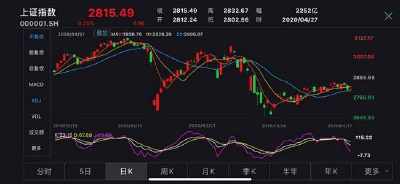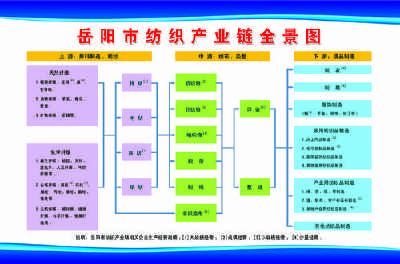角落里,农具歌
立春后,地里的点点跳跃触动着人们的神经。再过几天,地球的温度会上升,阳气会直线上升,地表下的一切都会异常活跃。
斧、凿、铲、叉缺一不可,每一件农具都是农耕文化的图腾。在土地上劳作是农民对庄稼和土地最好的崇拜。大地造纸,汗水作墨,仰望天空,接受大地,硕果累累的庄稼和秋收是他们过去一年最得意的作品。
西房里,墙角,一把把农具悄悄诉说着逝去的岁月。这些原始的农具,被时间侵蚀而变得诗意,这些笨拙、简单、沉重的农具,让无数农民弯腰的农具,是农民手中的笔。
(一)
阿木查站在泥胚老房子的墙上,两个木叉尖看起来咄咄逼人。木叉以犀利不羁的表情面对周围的世界,不像铁锹那么温和容易接受。它身上好像长满了刺,让陌生人不敢轻易靠近。它以傲人的身影站在南屋墙的一角,穿过“叮叮当当”的群山,穿过“吱吱”的岁月,这让它与同伴显得格格不入。
木叉的美好时光在夏秋两季,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,也是它在麦田里以矫健的姿态驰骋的时候。
打谷场上,一场激战正在进行。黑暗中,在打谷机的脱粒出口处,木叉被主人紧紧抓住,伴随着扔出的新鲜麦苗,木叉顺手摘下扔向两边,一个完美的弧线在模糊的夏夜中隐约闪现。随即,他起身准备下一波攻势,不急不躁。不一会儿,主人身后堆了一大堆麦苗,木叉在作者手里像绅士一样翩翩起舞。调皮的孩子不停地踩着草堆,突然踩上去,软软的麦苗下去了很多。大人见时机合适,便在两个木齿间做了一个高抛动作,里面全是木叉麦苗。草堆越来越高,渐渐无法直视。这是木叉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。
慢慢地,木叉锋利的木尖,像一道划过夜空的闪电,渐渐消失在广阔的村庄里。木叉慢慢褪成黄土的颜色,沧桑浑浊的眼睛一直望向麦田。木叉去哪里了?有些人心里在想。
(二)
把两把锄头悠闲地倒放在南屋墙角,一根木棍,一个铸铁锄头板。锄头结构就是这么简单。
锄头不像木叉那样咄咄逼人,难以接近,但对它更温柔。虽然相貌普通,体格虚弱,但锄头却把全部力气都积蓄在锄板里,以一种韧劲铲进泥土里。
锄头贴着地面飞得很快,“哧哧哧”。锄板所到之处,马齿苋全被砍掉,锄板毫不留情。锄头只追求实效,用最少的力气干最多的活,留给土地的只是地表的轻微颤动。
时间长了,锄头的铁皮慢慢变钝了,老农只期待村中心会打铁的铁匠,锄头会显得锋利。
孩子们在田埂上锄地,在田埂边抓人。
利的瓦片,蹲在地头间,“吱吱吱”地擦拭着锄板,铁片被尖锐的瓦片摩擦得锃亮,锄板上似乎映出了孩童被烈日烤红的脸颊。勤劳的人和锄头结合为了一体,锄杆越发光滑,锄板越发铮亮。遇到懒惰的人,锄杆粗糙无比,锄板生锈,庄稼多沦为荒地。锄板因光阴的变迁而变钝生锈,可在同岁月的斗争中,锄头一直伴随着老农,看朝阳露珠,望着不远处的阵阵炊烟。
(三)
“耙”,字从耒,从巴亦声,“巴”意为“附着、粘稠”,耒指农具,耒与巴相结合,即一种把杂草、堆肥、碎土摊开的工具。
在泛着麦香味的麦场上,一把木耙立在一边,呈现着如同一把木梳的样子。木耙从先辈那里流传下来,人们靠它劳动,从耙齿间,土疙瘩里,梳出柴米油盐,养家糊口。
木耙做事,总有一番较真劲,耙头所到之处,必定要细细翻动,不急不躁,无数次重复却依然耐心无比。
秋末冬初,西北风在“呼呼”刮,冻得行人直缩脖子。杨树林中,偶尔有几片和大树较真的残叶,在树梢处不服输地打着转。一位五十多岁身板壮实的老农,扛着耙,挎着麻袋走在前,一个小孩赶着步子紧跟着老农。寒风不断迎面吹来。村子北边横摆着一排小土屋,显得有些凄凉。小孩手里也抱着一包麻袋,看这架势,是要装不少叶子回家取暖了。为了在寒冬来临前更有底气,那位中年人每天都来耙几大包杨树落叶。
老农双手紧握耙,从树下快速地耙着,没过一会儿,耙起的落叶堆起了一座小山。小孩给麻袋撑着口,中年人不住地用手往里塞,蓬松的落叶占满了大半个袋子,双手扶着袋,用脚猛往里踹,又腾出一些空,抓起一把再往里塞。家门口摆放的一袋袋枯叶当柴禾。
而如今的乡村,耙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微妙,轰隆隆的收割机早已划破了乡村曾经的宁静安谧,滚烫的水泥路取代了曾经温馨热闹的打麦场,耙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,可它仍旧在回忆着过往生活的美好,星光闪烁间,是主人和它共同奋战的美好时光。
(四)
镢头,有一种敢为先的韧劲。镢头与锄头是忠实的兄弟俩,是西屋里墙角落的常客。镢头不似耙那样间歇性劳作、性格有些温柔。在乡村劳作中,一年四季都在发挥作用。
刨土、挖坑,庄稼汉挥舞着镢头,在空中划大半个弧形,狠狠地砸向地土地。每一次挥镢头,都是对清贫生活的愤怒,每一次高高扬起镢头,是对清贫生活的种种无奈,对幸福生活的无比渴望。
无数个炊烟袅袅的黄昏,父亲将镢头置于右肩,右手顺势握着木柄前沿,沿着果园里的小路往家里方向走。白天,他拼命地在地里挥着镢头,高高扬起,再掂一掂,拉开架势,趁镢头把在手里倒换的劲儿,朝手心里轻吐一口唾沫,抡起镢头便刨下去------“当啷”一声,虎口处发麻,膀子锁骨窝处震得直发疼,镢头露着厚重的铁片直插泥土。
看准时机,铁匠铺里的汉子来到了村子中央的空旷处,支起了摊子。
师傅先用锤子“叮叮当当”地敲上一串节奏,响脆声格外悦耳,村子四方都能听见。百姓扛起被磨得发钝的农具匆忙往村子中心赶,急切地想让铁匠给磨得锋利些。镢头被放在了被烧红的炭灶上,铁匠师傅在加速拉着风箱,“咕咚,咕哒”......待镢头烧红了,铁匠握着锤,搭档也逮着大锤,铁匠砸到哪里,另一把大锤立刻跟上,“叮叮叮......”当当当......”俩锤子发出的声音前后错落相融为了一体。
如今的农具,仿佛陆续完成了一种历史使命,静卧在角落处,倾听岁月前进的协奏曲。该去的一定会去,该留的必定会留下来,西屋里的件件农具,无论去留,都是最好的选择。
听,墙角落的农具在慢慢奏歌。